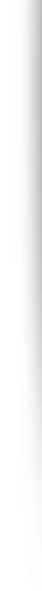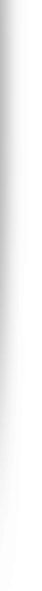盈科|解读 浅谈海难救助若干问题
已被浏览636次
更新日期:2021-06-09
来源:盈科律师事务所
近两年,“加百利”轮和“桑吉”轮案件引发海事司法领域对海难救助问题的关注与讨论。本人学识尚浅,难以对热点问题作出鞭辟入里的分析,但是借机看了一些判决书,对司法实践中的争议焦点问题略有所知。本文仅对个人学习成果进行梳理。
一、研究基础与争议焦点归纳
在“把手案例”数据库中,以“海难救助合同”为案由进行检索,共检索到12份判决书,其中“加百利”轮案有广东高院和最高院两份判决书、湛江海事局诉莱尔海外公司和广西先林公司一案有原诉讼和反诉两份判决书,所以实际共检索到10起案例。同时,在“北大法宝”以同样方法检索,剔除重复案例,最终共收集12起案例。此外,中国救捞创建60周年纪念系列丛书《水上救助打捞精选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也是重要参考资料。
海难救助案件争议问题大致有:海难救助合同关系是否存在、国家有关机关(如海事局)是否有权请求救助报酬、救助报酬金额如何确定以及相关证据的认定问题。
二、海难救助合同关系是否成立
合同是民事主体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根据合同成立是否以采用法定或者约定的某种形式为要件,可以分为要式合同和非要事实合同。
海难救助合同为非要式合同,被救助人发出要约、救助人承诺后即成立,不需要签订正式的书面协议。在(2012)广海法初字第959号案和反诉(2013)广海法初字第1122号案中,莱尔公司所属的“宾丹之星”轮在湛江港2号引水锚地搁浅,向湛江海事局交管中心报告、要求紧急救助之后,湛江海事局组织和指挥相关方进行救助。法院认为,莱尔公司要求救助属于要约,湛江海事局组织和指挥救助的行动构成承诺,双方之间的海难救助合同关系成立。
当然,现实情况可能更复杂。例如,在本人曾参与处理的一起案件中,被救助人的船舶搁浅后,被救助人经技术咨询同意由某公司负责脱浅作业,但要求该公司满足海事局对作业资质的要求。过后,因双方不能在价格上达成一致,该公司向被救助人索赔前期作业投入费用。经查,我们发现该公司不具备本次作业所要求的资质,我们主张救助人同意由其完成脱浅作业的协议是附条件合同,条件不具备,救助合同不成立。
关于国家有关机关是否有权请求救助报酬,实践中,船舶遇险后第一时间会向管辖水域的海事局报告,随后海事局组织和指挥有关救援力量进行救助。
救助结束后,海事局起诉被救助人请求支付救助报酬,而被救助人一般会抗辩称海事局属于国家主管机关,救助遇险船舶属于履行正常职责。这样的案例除上述湛江海事局诉莱尔公司和广西先林公司外,还有汕头海事局诉信盈公司和信诚公司一案(案号:(2007)广海法初字第352号)。在湛江海事局诉莱尔公司和广西先林公司案中,莱尔公司认为争议事项不构成海难救助,湛江海事局仅在履行其职责。在汕头海事局诉信盈公司和信诚公司救助报酬一案中,信盈公司所有、信诚公司经营的“信盈”轮在台湾海峡遇险,主机失控且遭遇大风浪,汕头海事局接到船长和信盈公司的求救信息后调派“海巡31”轮赶往现场组织有关船舶进行救助。为此,汕头海事局起诉信盈公司和信诚公司支付救助报酬。两被告的抗辩理由之一就是对“信盈”轮实施救助的是东海救助局,汕头海事局只是起到调查和处理作用。在两起案件中,法院最终都是以《海商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支持海事局的请求。
海事局是否有权向被救助方请求支付救助报酬,有两个问题要解决:救助遇险船舶是否属于海事局的法定义务;《海商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是否足以支持海事局请求救助报酬。
关于海事局是否有法定救助义务,从国际公约来看,我国加入了《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该公约1988年修订案第2.1.1条规定:“各当事国,在能够单独地或与其它国家合作和,视情而定,与本组织合作这样做时,须参与开展搜救服务的工作,确保对海上遇险的任何人员提供援助。在收到任何人在海上遇险或可能遇险的信息时,当事国的负责当局应采取紧急步骤,确保提供必要的援助。”而且,该公约开篇即说明公约宗旨,“本公约各缔约方,注意到若干国际公约十分重视对海上遇险人员的施救和每一沿海国家为海岸值守及搜救服务作出适当及有效的安排,考虑到1960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会议通过的第40号建议,该建议认识到在若干政府间组织中对海上及海空安全进行协作活动的需要,期望通过制定适应海运中救助海上遇险人员需要的国际海上搜寻救助规划来发展和促进这些活动,希望增进全世界搜寻救助组织间和参加海上搜寻救助活动者之间的合作,经协议如下。”可见,《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是旨在协调各缔约国救助人命的国际公约,并不包括财产救助。从国内法来看,《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一条规定:“为加强海上交通管理,保障船舶、设施和人命财产的安全,维护国家权益,特制定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主管机关接到求救报告后,应当立即组织救助。有关单位和在事故现场附近的船舶、设施,必须听从主管机关的统一指挥。”根据上述规定,为维护交通秩序,保障人命财产安全,海事局有组织救助的义务,但组织救助与实际从事救助不同。综合来看,海事局有救助人命的义务,这恰与《1989年救助公约》和《海商法》中关于单独救助人命无救助报酬请求权的规定相协调,而对财产仅是组织救助。
《海商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国家有关主管机关从事或者控制的救助作业,救助方有权享受本章规定的关于救助作业的权利和补偿。”本人认为,这里存在两种情况:国家机关从事的救助作业,根据该条规定有救助报酬请求权,没有疑问;但对于国家机关控制的救助作业,有权请求救助报酬的“救助方”仅指实际从事救助作业的主体还是指控制救助作业的海事局和实际从事救助作业的主体似乎规定得不够明确,而且这里的“控制”应该是与“从事”不同的一种情况,即组织救助而未实际从事脱浅、拖带等救助行动。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组织救助是海事局的法定义务。既然是法定义务,海事局就没有救助报酬请求权。
综上所述,海事局是否具有救助报酬请求权分以下情况:(一)海事局仅组织、控制和指挥救助作业,没有实际实施救助作业,海事局没有救助报酬请求权,实际实施救助作业的救助人有救助报酬请求权。但在这种情况下,不妨碍各实际救助人将其救助报酬请求权转让给海事局、由海事局统一行使(如上述汕头海事局诉莱尔公司、广西仙林公司案),不但可以避免救助人之间证据产生矛盾,而且还可以利用海事局收集证据便利的优势,实践中也常出现此类做法。(二)海事局组织、控制和指挥救助作业,并且实际参与、实施救助作业,如用海巡舰或者租用船舶转移货物或者拖带遇险船舶,此时海事局具有救助报酬请求权。但是,由于海事局属于国家机关,有政府的财政支持,利用自有船舶进行救助时成本比一般救助人低,所以在同等情况下海事局有权获得救助报酬相对较低,这一观点也是司法实践中基本得到认可的。
三、如何确定救助报酬
因为《海商法》第一百八十条只规定了确定救助报酬的十项参考因素,缺乏像第一百八十二条“特别补偿条款”那样定量标准,所以实践中救助报酬具体金额的确定往往是救助人与被救助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使得救助报酬金额问题就好像船舶碰撞案件中划分责任比例一样,很难准确判断。
总览各判决书,救助报酬主要围绕拖轮费用、人员费用展开,救助人和被救助人也是以此为中心举证、质证。下面就其中常见证据及其注意事项进行列举,供救助人和被救助人参考。
1.救助拖轮船舶所有权证书,证明救助人使用自有船舶进行救助。如果租用他船救助,要有相应的租船合同和租金支付凭证、发票。
2.拖轮的吨位证书,拖轮吨位是计算救助报酬重要依据。
3.拖轮工作时间证据材料,如拖轮从港口或者锚地起航至救助结束回到锚地或者港口的航行轨迹、航海日志、轮机日志、救助日志等。
因为拖轮费用计算是按照***元/马力/小时计算的,所以2和3结合可以证明拖轮使用费用。须注意的是:(1)救助方要保证上述证据材料向协调,不能自相矛盾,也不能与涉案其他相关证据矛盾,如在宁波甬洁公司诉营口北方船务公司和大连人保案(案号:(2016)浙72民初930号)中,宁波甬洁公司一方面称自2015年8月26日至2015年11月28日24小时进行应急处置工作,索赔全部期间费用,另一方《航海日志》记载在恶劣天气下船舶只能返航或者锚泊;宁波甬洁公司提供出勤表证明救助人员费用,但与单船日工作计划所列出勤人员人数不一致,最终未得到法院认可。(2)被救助人有时抗辩称,实际救助作业比原定救助方案简单,拖轮费率应有所降低。对此,本人认为从***元/马力/小时的费率单位可知计算拖轮费用的两个要素是时间和额定功率,无论救助作业难易,拖轮只是在一定时间内提供动力,救助作业难易并不是计算拖轮费用考虑的要素,实际救助作业较计划容易应体现在所使用设备和相应费用的减少、技术人员投入减少等方面,而且即使救助方案没有变化也不可能用尽拖轮的额定功率。(3)拖轮及相关设备收费时间,应分为工作时间和待命时间,且待命时间费用较工作时间费用低。(4)具体费率最好事先约定,如无约定,一般按市场价格计算。为此,可以提供相同时期最相类似的案件资料作为支持证据。
4.船舶设备清单和应急设备购置清单(及其发票),证明为救助所购置的额外设备费用。
5.每日工作单,建议救助人将每日工作单发送给被救助人(或遇险船舶船长)和海事局(如有海事局组织救助)签字确认。诉讼中,被救助人一般会否认该工作单记载内容,被救船长可能也不会签字,但如果能有海事局的确认对救助人来说可能会大大提高证据的证明力。
6.每日出勤人员统计表、工作人员身份证和技术人员资质证书,建议每位工作人员签字,同时发送给被救助人和海事局确认。其中,技术人员资质证书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技术人员费用较普通工作人员高,没有提供相应证书或者证书过期不能得动法院支持。
7.根据所有设备使用和人员出勤情况,制作最终的价格清单。
以上仅是对救助案件中主要证据的总结,由于海难救助案件常常涉及碰撞、打捞、污染等问题,所以还有很多其他相关证据需要涉案主体注意收集。
四、总结
救助案件中,否定救助关系的案件很少,争议焦点主要还是集中在助报酬问题上。“无效果、无报酬”是确定救助报酬的基本原则(“桑吉”轮救助人境遇似乎不乐观),而救助报酬具体金额的确定主要靠救助人举证。所以,对救助人来说,收集证据与救助作业同时进行且同样重要。
作者简介:滕立夫 律师